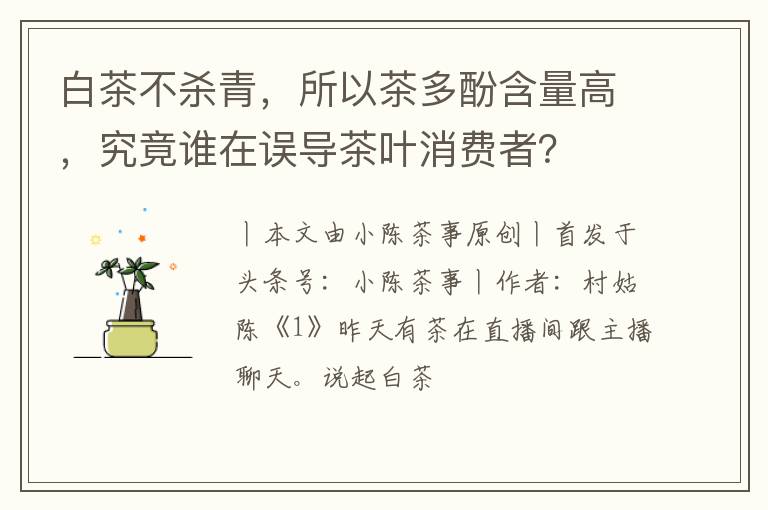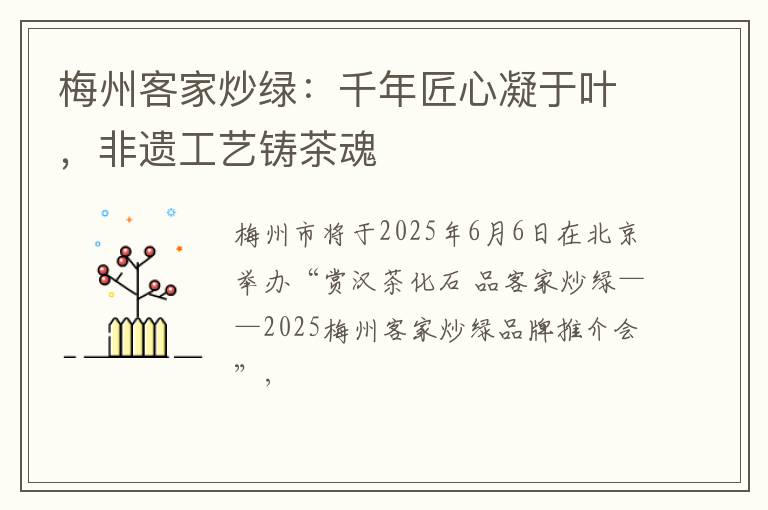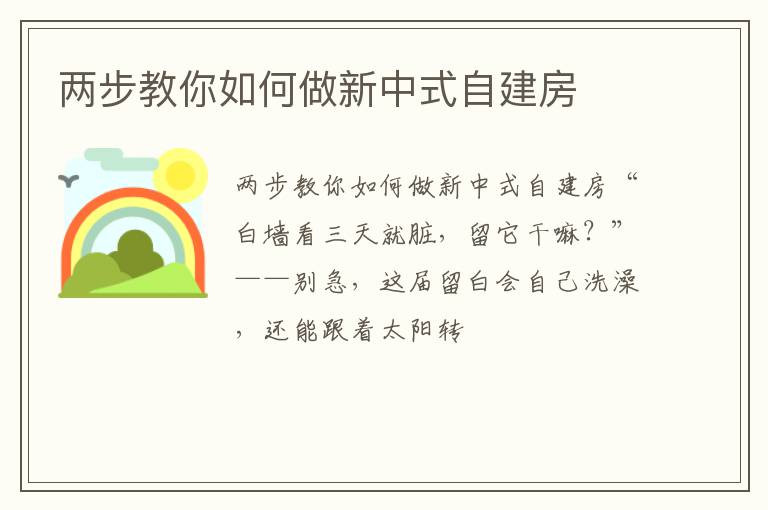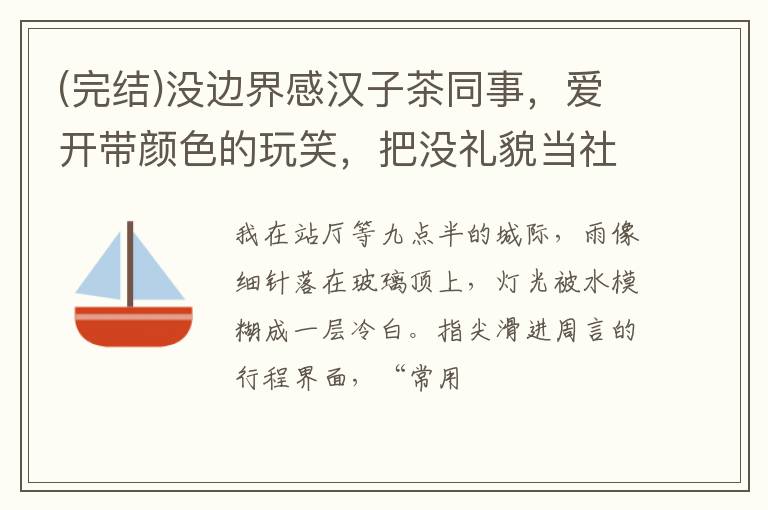
我在站厅等九点半的城际,雨像细针落在玻璃顶上,灯光被水模糊成一层冷白。
指尖滑进周言的行程界面,“常用同行人:小安”,备注是他自己加的,像一枚清晰的霓虹插在我的眼里。
列车进站前一秒,我把手机合上,心里像有人拧紧了一个旧灯泡,发出几下不甘心的咯吱。
我站在白光和黑洞的交界,耳边轰鸣在逼近,我知道该做的不是吵,是记。
我不是善良,我是不喜欢脏。
时间提示:两天前。
雨没有来,天却阴着,我在公司走廊里遇见韩子茶,他端着自己的紫砂壶,像舞台上的司仪。
他爱开带颜色的玩笑,见我就点着自己的腰,冲我笑:“顾姐,昨晚谁把你折腾成这眼圈了?”
我抬眼看他,平平地说:“你要被投诉。”
他笑:“别这样,咱们都是自己人,社牛嘛,活跃气氛。”
他的笑里有没礼貌的自信,他把粗糙当热情,人群被他带着起哄,像被不合适的音乐牵着脚步。
我胸口的玉坠贴在皮肤上,压住了不必要的冲动。
我拎着餐盒从他身侧过去,里头是早上熬的牛骨汤,油花在汤面上一圈一圈地靠近,又被我拿勺子轻轻划开。
我在会议室的门口停下,有人从里边出来,挡住我的路,碰在我的肩上,肩线被挤出一个小弧。
生活像法庭,处处留证。
两天前的晚上,家里锅里煮面,蒜末扑在油里“吱”一声,我站在灶前,周言从后面把我环住,吻我的后颈。
他问:“明天你要去站厅接沈总吗?”
我说:“不接,改线上了。”
他“哦”了声,手落在我的腰上,动作缓慢,我把火调小,让面再泡一下。
我们结婚七年,在第三年时做了第一次试管失败,在第五年做第二次,胚胎没熬过那个抽血日。
那一天我把石榴放在桌上,母亲说多子多福,果实红而轻,却压不住我们家的空。
周言说:“没关系,就我们两个也很好。”
我听见他喉结滚动的声音,眼眶发涩,但手上做事无比准确地挑起一筷面,把汤倒进碗里。
这一次,我没有问他是不是又用我手机叫车,我也没有给他看我的出行账单,我们在表面的平静里吃完面的那一刻,生活像和合的热汤。
两天前的中午,韩子茶在群里发了一张短视频,桌上放着一杯乳茶,他拿吸管在杯子口摸来摸去,配文:“姐妹们,吸管要从这儿插进来才顺。”
大家笑了一阵,有人说他嘴贫,有人说他嘴甜。
我看完视频,把它保存下来。
我把时间当硬币一点点投入,换取靠近事实的权重。
下午的走廊白光很刺,照得他脸上天生的放肆更明亮,他叫住我:“顾姐,晚上聚餐,周言来不来?”
我说:“他不来。”
他眨眼:“你们家周言最近挺忙的吧,常和一个小姑娘一起打车。”
他的语气像随意投掷的石子,砸在水面,溅起一点浮沫。
我看着他笑出来,那是我训练出来的礼貌:“你挺爱管别人家事。”
他“呵”了一声,没见我怒,就更顺理成章地凑近一步:“我这人啊,没边界,但心不坏。”
我说:“你心好不好不重要,重要的是规则。”
他怔了一下,像临时被人拿出一张他没读过的卷子。
这天晚上我在书房,把家庭财务的表格又打开了一遍,备份在U盘里。
我把“共同财产”的栏变成蓝色,把“重大开支确认”的条标注为红色,我的手指头稳得像在抄法律条文。
我不是沉迷控制,我是要给我的生活一个契约化的外框,因为温柔和善良都不够抵抗没边界的事情。
回到现在。
站厅里风从列车尾过来,带着一种铁的气味,我的玉坠被吹冷,我把衣服领口拉了拉。
我打开手机相册,翻向那个保存的短视频,韩子茶握着吸管,笑得像一个年轻父亲在教孩子,但内容恶心。
列车到站,门开合,我没上车,我在白线后站着,看人群涌出又涌入,我的眸子像一个不焦躁的镜子。
我在心里把流程排好:事件触发,调查确认,公开呈现,冲突谈判,规则重构,缓和修复,尾部反转。
案件不是婚外情,至少事实未必,但它是边界的塌陷,裹着笑声和疲惫。
我拨周言,声音被列车吞了一半:“等我到家,我们谈谈。”
他沉默两秒:“好。”
他没问“关于什么”,像心里有一个篡改过的日历。
我走出站厅,雨更大了,打在我发梢,像有节奏的审问。
时间提示:晚上八点。
锅里的汤我重新热,藜麦菜叶和豆腐已经入味,汤的油花像被训练过的队列绕着碗走,“面”被我最后才下,留着嚼劲。
周言在餐桌边坐下,喉结不时轻轻地上下,看起来像在噎住没说出口的东西。
我放他的碗在他面前:“吃。”
他拿起筷子,手微微发抖,我观察而不评价。
他喝第一口的时候,我把手机放在桌面,屏幕朝上,“常用同行人:小安”,备注“公司同事”。
他的喉结走了一个大弧线,我听见碗边发出轻微的碰瓷声。
我们不在公共场合撕,我们在家里谈,克制是义务,不是恩赐。
我问:“她是谁?”
他说:“同事,行政组,安晴,小安。”
我点头:“你们为什么常一起打车。”
他说:“加班到很晚,她住在我路上。”
他眼神在汤面上停着,像在找一个可以套牢他的浮木。
我问:“备注是你自己加的?”
他点头。
我说:“你婚姻里的忠诚义务,包含界定关系,公开透明,避免让伴侣合理产生怀疑的行为,你知道吗?”
他的手落下筷子,发出一声小声的叹:“我不是要你怀疑。”
我说:“怀疑不是一种意图,它是事实的条件,你创造了它。”
他抬眼看我,眼里有抱歉,也有防御,他说:“顾行,我真的只是顺路,我没越线。”
我说:“你在群里谈别人的私事,是越线;你在备注里给同事起更亲密的称呼,是越线;你没向我讲明,还是越线。”
他沉默,我把面条挑起来,单独放在一个小碗里,这个动作让我自己冷静。
生活像法庭,我给事实做分类,不因为爱而模糊证据。
周言说:“韩子茶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。”
我说:“他生活里没边界,把没礼貌当社牛,但我没拿他的话作为证据。”
他:“我就是怕你误会。”
我笑:“误会是未经证据的判断,到目前为止,我有证据。”
他抿唇,肩线垮了一点,像山洞里出来的人,眼里从白光走进黑暗。
我把一个厚厚的透明文件袋放到桌上,里面是我们过去两年的打车记录、餐饮记录、酒店账单(没有异常)、对公项目的报表,还有一张空白的纸。
周言看着这些东西,一种被审视的脆弱在他脸上跑出一条细细的纹路。
我说:“我们写一个补充协议。”
他抬眼,喉结猛地动一下:“协议?”
我说:“婚姻是合同,不止是情感;合同里有条款,有违约,有修复;你不惯用语言表达,就用文件。”
他看着我,又看着那张空白纸,我很清楚他的害怕,不是害怕签字,是害怕承认婚姻不再是柔软的诗。
我把笔放在他的手边:“条款一,共同财产透明;条款二,重大开支预先告知,并在约定限额内共同决策;条款三,忠诚义务,避免与特定第三者发生超越工作需求的密切往来,比如长时间单独相处,频繁搭乘同车的行为;条款四,违约责任,若违反条款三,涉及精神损害的赔偿和财产分割优先倾向于在不利方承担;条款五,沟通窗口,每周一次面对面沟通,不得以加班等理由推诿。”
他听着,目光在汤面上像有一个固定点,每一个词都是在他心上插入一个针。
我停了一下:“你有补充?”
他摇头,嘴唇发白:“我做得到。”
人到了某个年纪,答应几件看似简单的事情,比学一个新技能更难。
我说:“我们先把事实做完。”
次日早上,走廊白光更亮,雨停了,楼下有叶子带着水,一滴滴地滑。
我把韩子茶约到茶水间,没有人,他端着壶,笑:“顾姐这么私下叫我,终于知道谁能把你逗笑了?”
我说:“你知道我们公司有边界倡议吗?”
他笑:“那东西就是给新人看的,你看我混到这份上,还需要倡议?”
我说:“你在群里发的视频,已经被我保存,性暗示,对女同事造成不适,属于性骚扰的范畴。”
他怔了一下,笑容斜了一点:“哎哟,你别这么上纲上线。”
我说:“我不是善良,只是不喜欢脏。”
他要开口,我在他前面把一份打印出来的《职场边界倡议》放在饮水机上,内容包括不在公共渠道发表性暗示,不在私下对同事身体进行评论,不以活跃气氛为理由触碰别人。
我说:“你签吗?”
他看看纸,又看看我,眼里开始有怒:“你觉得你是谁?”
我说:“我是受你影响的同事,也是这个职场的共守规则的人。”
他笑,笑得恶狠狠:“你是不是因为周言,想在公司找一个出口?”
我看着他,没生气:“生活像法庭,任何论证都需要证据,你这句断言,没有证据。”
他盯着我的眼睛,一秒,两秒,他没在这个时刻获得他喜欢的情绪反应,他开始不安。
我把一支笔递给他:“签或者不签,都可以;不签,我会向HR提交报告;签了,你就承诺克制,这不是恩赐,是义务。”
他咽了一口唾沫,喉结滚了一下,脸上的笑僵住了,转向自己的紫砂壶,像从中获取某种胆量。
他在倡议书上签了字,字歪却收尾有力。
我把纸收回,放进透明文件袋,这个袋子里,也会装下后面许多说过的话。
时间提示:下午三点半。
安晴的办公位在靠窗的位置,她的椅背上挂着一件灰色的针织外套,很干净。
我让她到会议室,她握着杯子进来,杯子上印着“夏天和柠檬”,她问:“顾姐,找我?”
我说:“是,我们三个人谈个事情。”
她怔一下,目光里有被叫进老师办公室的小心,她看向门口,周言已经走进来。
我在桌面摆三杯温水,没有咖啡没有茶,透明的水像判决书的格式。
我把文件袋放在桌上,平静地说:“第一,我知道你们常一起打车;第二,你是备注里的‘小安’;第三,我没有证据显示你们的关系超越工作,但我们的婚姻里有条款,也许会涉及你。”
她的脸发白了一瞬,又很快恢复,声音很轻:“我知道周总有家,我没有……我没有要越线。”
周言看着她,像在用眼神维持礼貌的宽容,又像在对自己说话:“她住在我路上,顾行。”
我把目光转回来:“接下来是规则。”
我拿出一份杜撰的、但写得像法律文本的《婚姻补充协议接触条款说明》,我对安晴说:“这不是约束你,这是我们之间的约束,你作为当事方之一的工作关联人,有权知道并选择合作方式。”
她点头,肩线有一点紧,手指在杯子上抠着那枚柠檬图案。
我说:“从今天起,除非项目明确安排,不在下班后单独搭乘同车,不在非公场合以更亲密的称呼交流,不在任何时间以浮泛的情感词作为工作配合的纽带。”
我的语气像在读条的训示,但我尽量把每个字放在柔软的毯子上。
她说:“我可以做到,我不想……我不想让人误会。”
她眼睛里有年轻人的明亮和怯生,她坦白她需要安全感,她说:“周总对我工作很照顾,我就觉得很安心。”
周言低头,像被一句长且轻的词敲在头上,他说:“我不会再让你承担风险,安晴。”
我把纸合上,完成了公开呈现和冲突谈判的第一部分。
我们没有当众撕,我们只在今天的白光里重排规则。
我对周言说:“你带她去组里会议,把安排交代清楚,卡在安排的边界里做事。”
他点头,他眼里有一种小的虚弱,却为这虚弱找到了策略。
安晴出门的时候,门铰在她手下发出一声轻微的“吱”,像一条被拉紧的线。
时间提示:晚上十点。
家里的锅洗干净了,我把汤的剩下部分倒掉,洗得像法庭的证物要回库。
周言把衣服脱到椅背上,肩线在灯下成一个半圆,我把玉坠从领口拿出来,放在桌上,玉是从他母亲那儿来,她说玉能护人。
我们坐在客厅里,灯换过一次,婚姻像房间的灯泡,如果一直发黄,就要换。
我说:“你今天做得不错。”
他看着我,眼里不再闪动,他说:“顾行,我累。”
我说:“累是我们的日常,累不是越线的理由。”
他笑一下,笑得像被风吹过的烛火,没火花,只有热气:“有人说我家像黑洞,资源进去都不见,努力进去都被吞。”
我看着他,感觉到他在用一个比喻逃避现实又逼近现实:“我们的家不是黑洞,但有空的时候,声音会被吸进去,你害怕你说话会没有回声。”

他叹气,像从山洞白光走进黑暗,又走到另一头的白光:“我就想有人和我顺路。”
我说:“你可以和我顺路。”
他抬眼,看着我,像在问一个孩子问题:“你不在的时候,我就一个人走。”
我心里的一块东西被他放轻,我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,手指头的骨关节在灯光照下显出一条条线。
我说:“我们做柠檬水吧。”
他怔:“什么?”
我说:“我们把生活里的柠檬,挤掉苦,往里加糖;这不是自欺,是改变量化让关系回温。”
他笑出来,笑很短,像刚才那条线的另一头有一颗小灯泡亮了一秒。
时间提示:第二天。
韩子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,喝茶,他又开群聊,把一个新来的男生的照片放出来,笑:“将来这小子怕是要迷倒公司一片。”
他面前的人群涌动笑声,我停在不远的地方,看着他像一个舞台上的人,他需要掌声,他从掌声里找在这里活着的证据。
我把文件袋拿出来,里面还有那张倡议书复印件。
我走到他的桌前,轻声说:“我提交了报告,HR会来找你做沟通。”
他抬眼,笑脸有了几条皱纹:“顾姐,要不要把你家务事也写进倡议里?”
我看着他,声音很干净:“我家务事已经写进合同里了。”
他挑眉,显出一点不屑。
我补一句:“我没有要毁你,我是要保护其他人。”
他突然沉下来,喉结滚动一次,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,像要把脾气压回去。
他旁边的茶壶发出一声响,盖子轻轻碰到壶口,这个声音像一圈小小的警钟。
时间提示:日暮。
我去菜市场买了骨头,买了两根葱,买了一个石榴。
奶奶说石榴孕满子,拿回家放在桌上,像一个红色的未来,但我们的未来从来不被果子逻辑化,我们用慢慢的改变去填那一个空。
回到家我把石榴放在盘子里,还在桌上发出亮晶晶的光,我对着它拍了一张照片,发给母亲,她回复:“亮。”
我把汤炖上,锅里的水一开始不安,一个一个气泡冒出,后来就稳定,像结论。
我把时间当硬币投入,火是恒定的人性,汤是需要耐心的证据。
周言回来,站在门口,靴子上带雨点,他把伞放在门口,伞滴水,我拿布擦了一下。
他走过来抱我,他肩线沉下来,他说:“今天我把项目分层了,下班后不会跟人一起走太晚。”
我“嗯”了一声,接受这个变化的可观察证据。
这时候手机响了一下,我看过去,是安晴发来的消息:“顾姐,我把备注改了,改成‘周总’,谢谢你教我。”
我回复:“记得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边界。”
她很快回:“我会,我想做明亮的人。”
我对着手机笑了一下,笑得短,像白光和黑洞之间所能维持的温度。
时间提示:一周后。
公司里有一个早会,韩子茶被HR叫出去谈,回来之后他没有再发任何关于身体的玩笑,他在喝茶的时候反复看杯子,好像在穿越自己的坦率和粗鄙。
我不是要他改成另一个人,我是要他学习合适。
那天晚上我回家,周言在厨房洗锅,他的背影小而认真,水流在他手上滑过,他的肩线和背线仍然有疲惫,但不像负担。
我摸摸我的玉坠,它在我的指尖上滚动,像一个正在恢复温度的物件。
我把面下进锅里,面浮上来的时刻,我把它拨开,蒜末在油里发出“吱”的声音,那声音像小时候走廊白光下母亲叫我吃饭。
我们坐在桌边吃,这一次,我们没有沉到不必要的沉默里,我们把事情当做一件已经被归档的档案,有入口,有出口。
周言说:“我和安晴说了,项目结束后把资源调走。”
我说:“好的。”
他又说:“我在手机里,把常用同行人的条删了。”
我说:“不要删,你不能删证据,你要改变事实。”
他停一下,眼神里有羞愧也有笑:“我知道,我只是……我想清一下。”
我说:“你清空的是你心里的不安,我知道,但我们的生活像法庭,要让证据存着。”
他点头。
我们吃着面,他抬眼看我的时候,我看见他眼里没有躲避,没有隐藏,他就像被换了灯泡的房间,照明是正常的。
时间提示:两周后。
周末的雨,像上次那样密,我在站厅等一趟去郊区的车,我们计划去看枫叶,像给这个从夏到秋的时间做一个颜色的证书。
列车轰鸣,他站在我旁边,我们没有说太多话,但肩膀靠在一起,这是我们选择的沉默,是修复的另一种语言。
我的手机跳了一下,是母亲发来的照片,她把石榴拆了一半,粒粒分明,她写:“你来吃。”
我笑着回:“下周。”
我们像把柠檬挤成柠檬水一样,把石榴也拆成了可以入口的甜。
周言的手机也响,他看了一眼,说:“公司群。”
我不看,也不问,我把玉坠从衣领里拉出来,他触摸它,像触摸一个约定。
时间提示:一个月后。
我们的沟通窗口被固定在每周四,八点,我把这条放进日历里,它像一个灯泡的开关,在每次按下的时候保证我们有明亮的时刻。
周言有时会说他累,有时会说项目的黑洞,我说:“我在这里。”
他抬眼看我,像是把一枚硬币投入我的时间里,看它滚过弯曲的轨道。
我把每一枚硬币存档,像给我们的生活建立一个统一编号的证据库。
他开始不再夜里回家在门口踌躇,也开始离家时学会说一个完整的句子:“我去公司,晚饭在外。”
这都是小的改变,微不足道,但可观察。
时间提示:季度末。
职场里有一个年度的评审,CEO站在台上讲边界倡议正式升级为制度,公司要做一个明亮的地方。
台下有人鼓掌,我也鼓掌,我的手掌心出汗,我知道这不是全因为这件事,但这件事的微小推动,在这个舞台上被看见。
韩子茶坐在后排,他没有笑,他拿笔做笔记,他抿唇,他用一种不习惯的方式,用安静填他的存在感。
我走出会场,在走廊白光里给周言发信息:“你今晚几点到家?”
他回:“七点。”
我回:“好。”
时间提示:晚上七点。
我的锅里煮鸡汤,汤连给两次,把浮沫撇掉,汤清而有味。
周言回家,他把一袋石榴放在桌上,笑:“买太多了。”
我把玉坠放在桌上,让它把我们的桌子变成一种被祖辈看着的地方。
他抽出一张纸,递给我:“财务计划,我把我的工资细项都列了出来,我的卡密码你也知道。”
我接过,看到每一个数字都像一个绳子的结,结和结之间没有秘密,他们只是被时间绑在一起。
我说:“谢谢。”
他说:“这是合同的一部分。”
我们把合同里的条款从纸上搬到生活里,它们像灯泡被插进房间,发生了热和光。
时间提示:年末。
我们的家没有孩子,但有规律,有汤,有面,有石榴,有玉坠。
每一次开煲,每一次挑面,每一次切石榴,都像在做一个审慎的仪式,婚姻就是把仪式变成生活,把生活变成规则,把规则变成温度。
我和周言去母亲家,母亲把石榴放在酒柜上,笑着说:“忙就不生也好,照顾好自己。”
我说:“嗯。”
我不是不想孩子,我只是比想生更想把我们两个的边界守好。
时间提示:春节。
公司休假,韩子茶给群里发了一个消息:“祝各位新年快乐。”
他的消息没再带颜色,也没再带粗俗,它像一杯清茶。
有人回应,我也回应,我说:“同乐。”
他私信我:“你那份倡议书,我又抄了一遍,给我老婆看。”
我回:“好。”
他发一个笑脸:“我老婆说你像老师。”
我笑:“老师也是要写合同的。”
他发个大拇指,然后就没了。
春节那天我在厨房,炸藕盒,油花行列整齐,小小的泡像深井打起来的水,滚烫而有秩序。
周言在灶台旁给我盛汤,他手背的青筋在灯光下像一条清线,他的时候我会像在看证据那样看他的手他的肩线他的喉结,他的每一个微小的改变是我的可观察证据。
时间提示:清明。
雨小了,路上落叶,我再一次站在站厅白光底下,这一次我不查“常用同行人”。
我把手机放进包里,我观察人,我看一个穿灰外套的年轻女孩抱着一束黄色的花,她的肩线一样紧,她像安晴,但不是她。
我站在白线后,我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靠花和雨活着,我们是靠一个个条款,一个个摁住脾气的瞬间,一个个克制是义务的叮嘱活着。
列车过来,轰鸣像一个从过去到现在的证词,我不急,我以我的步子走。
时间提示:五一。
我们去郊区过了一天,风从山洞的白光里穿过另一头的黑暗,又到白,像婚姻的路,有进有退,有光有影。
我们坐在某个坡边吃面,周言把玉坠捏在手里,说:“我觉得我慢慢明白怎么做一个有边界的人。”
我看着他,笑:“边界不是墙,是桥。”
他抬头,看这个桥,就是这一条路的弯。
时间提示:盛夏。
公司的冷气强,走廊白光更白,人闲着时会变得不那么克制,那些没礼貌的玩笑在这个季节最容易冒出来。
我在茶水间看到有人在笑一个女同事的裙子太短,我把倡议张贴在墙上,我没告诉HR,我只是让每一个经过的人看到。
韩子茶停在前面,他看着字,点一下头,我看见他抬手把那个童稚的嘴角压住,这是一个稽查证据。
晚上回家,我把汤冷着喝,冰汤像在心里搭一个冷的桥,从一头到另一头不会被热过头的感情打断。
周言看着我,把手放在我的背上,他说:“我们一直走。”
我说:“嗯。”
时间提示:开学季。
母亲打电话说她的朋友的外孙满月,我听见电话里笑声,我没有落入那种笑的标准答案里,我不是酸,我是在做我的柠檬水,我把生活变成对我可口的东西。
周言在我旁边看报表,眼睛里有种认真,他不像以前,他用了条款去控制他的临时冲动,他用了合同去提醒他不忘。
时间提示:中秋。
我们买了一个小小的月饼,切开,放在盘里,盘旁边放着玉坠,玉坠是圆的,月饼也是圆的,我在这种圆里看到一种自我完成的意味。
我们吃罢,坐在阳台上,夜风没有季节的坏脾气,它温柔而交付。
周言说:“你觉得我们这段时间的改变是有效的吗?”
我说:“改变是可量化的,减少夜归、减少异性交往频次、增加沟通次数,这些都是数据。”
他笑:“你把生活数据化。”
我说:“是的,生活像法庭,处处留证,这是我们的方式。”
他靠在椅子上,肩线放松了一点,我看见他喉结滚动不再紧张。
时间提示:寒露。
气温降了,汤更常出现,它像一条暖线,把我们的房间分割出细小的区块,每一块都被温柔的规则覆盖。
我们在某一个晚上讨论旅行的计划,我们把钱从一张表格分配到另一张,周言没有逃避,他是参与者。
这一天,我收到安晴的留言:“顾姐,我要调到另一个部门了。”
我回:“祝你顺利。”
她回:“我找到了自己的边界。”
我没有发别的话,我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明亮不是需要我的祝词,她的明亮是她的选择。
时间提示:立冬。
我们把厚衣服找出来,玉坠在很冷的时候更能贴着皮,我把它放在领口,它敲了我的骨头,像提醒我这一年已经走过不可逆的路。
周言在厨房把锅口里的水倒掉,他换一口新的水,我们把汤做成另一个时间的味道。
这时我的手机亮了一下,屏幕上跳出一条短信。
它短促而在白光里暗暗有力:“顾姐,有人说周总最近很近,备注里出现了一个‘阿青’。”
我的手指停在屏幕上,汤在锅里翻滚,它的声音像某一条在我心里刚刚搭起的桥被一个新的石子砸了一下。
我抬眼看周言,他在灯下,肩线稳,喉结平,他看见我手机亮,他问:“怎么了?”
我把手机锁屏,我没在这一刻撕,我把证据放在文件袋的空位里,我的生活像法庭,我的案件永远都在进行中。
郑重声明: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,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,多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