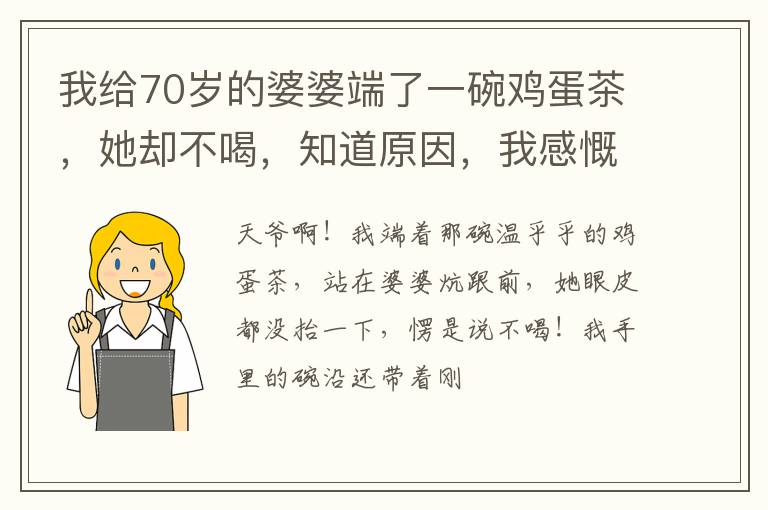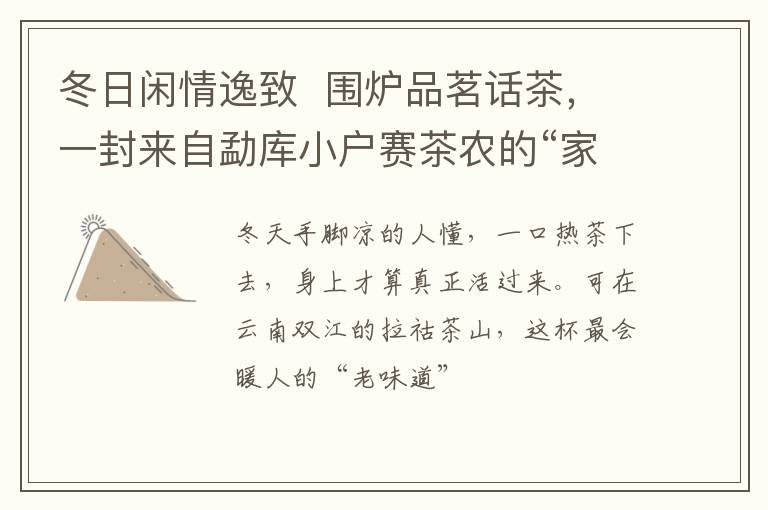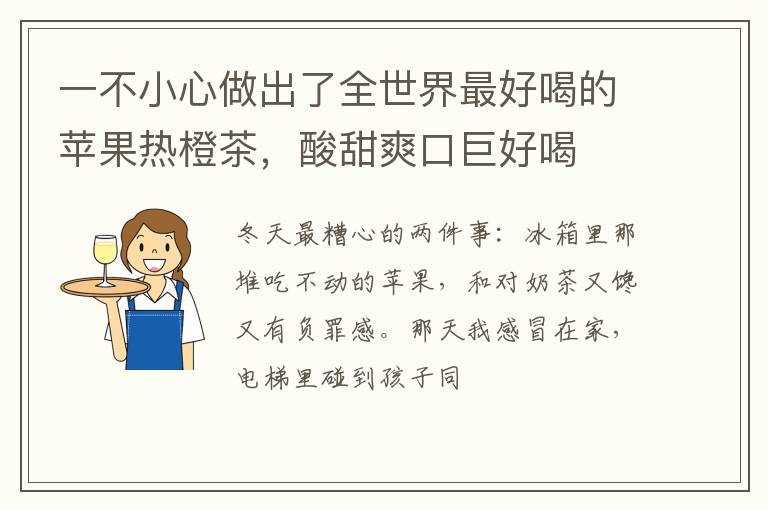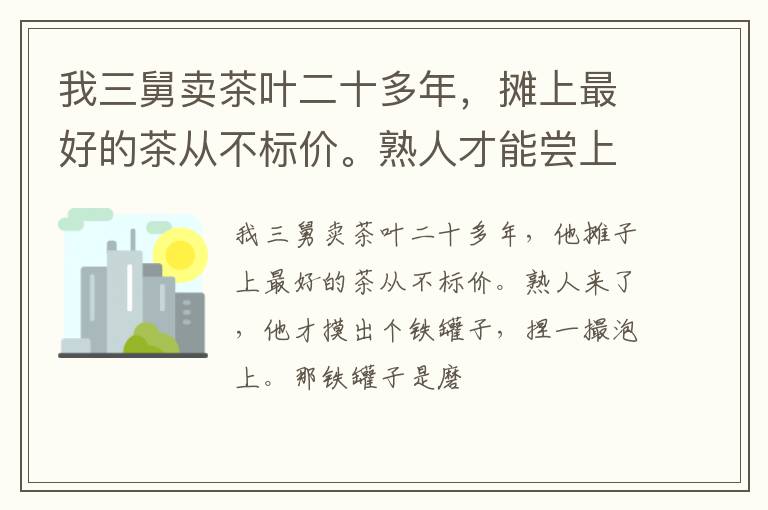
我三舅卖茶叶二十多年,他摊子上最好的茶从不标价。熟人来了,他才摸出个铁罐子,捏一撮泡上。
那铁罐子是磨砂的,看着不起眼,边角都磕出了白印子,却被三舅擦得锃亮,跟摊子上那些印着烫金大字的礼盒摆在一起,透着股格格不入的倔劲儿。我小时候总蹲在摊子旁边,盯着那罐子出神,问三舅里面装的是什么好茶,怎么连价都不标。三舅总是笑眯眯地敲敲我的脑袋,说这茶不是卖钱的,是卖缘的。那时候我听不懂,只当他是故弄玄虚,直到去年冬天,我才真正明白这话里的滋味。
三舅的茶叶摊摆在老城区的巷口,旁边是个卖糖炒栗子的大爷,再往里走,是一家开了三十年的面馆。二十多年来,三舅守着这个摊子,从满头黑发熬到两鬓染霜,摊子上的茶叶换了一茬又一茬,唯独那罐不标价的茶,始终放在最里层的货架上,像个藏在时光里的秘密。熟客们都知道这罐茶的存在,有人好奇问过价,三舅只摇头,说遇不上懂的人,给多少钱都不卖。也有人不死心,软磨硬泡想尝一口,三舅拗不过,会捏一撮泡了,但喝完之后,那些人要么咂咂嘴说没尝出啥特别,要么嫌味道太淡,远不如几百块一斤的龙井顺口。
我妈总说三舅傻,放着赚钱的生意不做,守着一罐破茶当宝贝。三舅每次都只是笑笑,照旧每天清晨五点起床,骑着那辆半旧的三轮车,载着满车的茶叶和茶具,慢悠悠晃到巷口摆摊。他泡茶的手艺是一绝,紫砂壶烫得温热,茶叶投进去,沸水一冲,茶香能飘出半条巷子。路过的行人闻到味儿,总会停下脚步,买上二两毛尖或者碧螺春,三舅从不看人下菜碟,收的钱比茶叶店里便宜不少,秤却给得足足的。
去年冬天,天气冷得邪乎,巷口的风跟刀子似的,刮得人脸生疼。卖栗子的大爷早早收了摊,面馆里也没几个客人,三舅却照旧守着摊子,拢着袖子坐在小马扎上,看着路上稀疏的行人。傍晚的时候,巷口走来一个老人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,手里拄着拐杖,步子走得很慢,走到三舅的摊子前,停了下来。老人没看那些摆着的茶叶,而是目光灼灼地盯着货架最里面,问三舅,那罐茶,还在吗?
三舅愣了一下,抬头打量着老人,眼神里先是疑惑,随即慢慢变成了惊讶,最后化作了一抹温和的笑意。他站起身,小心翼翼地把那罐磨砂铁罐子拿出来,拧开盖子,一股淡淡的茶香飘了出来。那香味不浓,却很清冽,像是初春的第一场雨,落在刚冒芽的茶树上,带着股沁人心脾的凉。三舅捏了一撮茶叶,放进紫砂壶里,沸水冲下去,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,汤色是淡淡的黄绿色,看着就让人心里平静。
老人坐在小马扎上,端起茶杯,轻轻抿了一口,闭上眼睛,半晌没说话。我刚好去给三舅送棉袄,站在旁边,看着老人眼角慢慢渗出了泪花。三舅递给老人一张纸巾,没说话,只是安静地陪着他喝茶。那一晚,两个老人坐在巷口的茶叶摊前,喝了一壶又一壶的茶,从傍晚聊到深夜,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后来我才知道,那罐茶的来历,藏着三舅半辈子的念想。三十年前,三舅还是个毛头小子,跟着老师傅在山里种茶。那年春天,山里发了洪水,老师傅为了救那些刚冒芽的茶树苗,被洪水冲走了。临走前,老师傅塞给三舅一个布包,里面包着一小撮茶叶籽,说这是他一辈子心血培育的品种,性子淡,耐泡,要等懂它的人来喝。三舅把那些茶叶籽种在山里,守了十年,才收获了第一批茶叶。他舍不得卖,就装在这个铁罐子里,等着有人能喝出茶里的故事。
而那个老人,是老师傅的师弟,当年和老师傅一起研究茶种,后来因为理念不同分道扬镳,一走就是三十年。他听说老师傅有个徒弟在老城区卖茶,特意寻了过来,没想到真的找到了这罐茶。
那一晚之后,老人又来了几次,每次都和三舅坐在巷口喝茶,聊着山里的日子,聊着那些关于茶叶的往事。再后来,老人带着三舅的茶叶,回了山里,说要把老师傅的茶种发扬光大。
三舅的茶叶摊依旧摆在巷口,那罐不标价的茶,还是放在最里层的货架上。我再问起三舅,这茶到底卖不卖,三舅还是那句话,卖缘不卖钱。
前几天,我路过巷口,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摊子前,盯着那罐茶看了很久,然后对三舅说,爷爷生前总念叨,说老城区巷口有罐好茶,能喝出岁月的味道。三舅笑了笑,又摸出了那个磨砂铁罐子。
阳光落在罐子上,反射出淡淡的光。我站在旁边,突然觉得,这罐不标价的茶,哪里是茶啊,分明是三舅守了二十多年的念想,是一段藏在茶香里的旧时光。这世间的好物,不都是这样吗,遇得上是缘分,遇不上,就安安静静地守着,等着下一个懂它的人出现?
郑重声明: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,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,多谢。